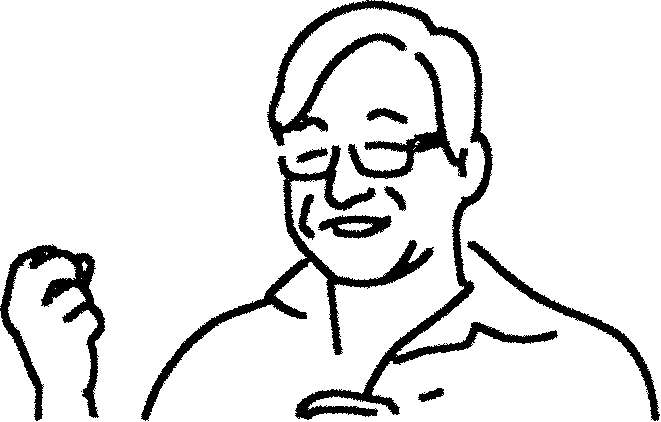

跑道上的白線一條一條工整而規律地貫穿橢圓形的紅土,在夕陽的餘暉下顯得特別耀眼,不禁讓我想起幾年前的護士阿姨曾經對我說的:「白的白,紅的紅,綠的綠」,擔任學務主任那幾年學校進入重建期,操場每天被砂石車輾來輾去的,都成了廢墟,現在新校舍成了一煥然的風貌,而草場也不須再承受大型機具的蹂躪,也不再塵土飛揚,學生可以恣意在鮮紅的步道上散步,也可在如茵的綠上丟飛盤、踢足球。 
坐在看台凝望著這一幕,突然想起我的農耕隊成員。這群學生大多孔武有力,而且重義氣,平常沒有場域可以發揮所長,於是我找他們來綠美化校園,並讓同學們知道他們對學校的貢獻,每次只要他們把難處理的樹幹、雜草處理掉,放學時我一定請大家蹲下,一一唱他們的名,讓他們被瞻仰,也讓他們知道「我也可以被稱讚,被肯定!」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,這批孩子大多不是自己喜歡叛逆,而是他們有一個叛逆他們的環境,能跟這樣的環境奮戰了十幾年,真的不容易,如果學校不是另一處能讓他們喘息,甚至提供助力的地方,他們哪來的能量繼續抗戰。 有次剛放完暑假,建築物後方雜草叢生,而且有很多姑婆芋,負責清掃的班級叫苦連天,而且一個接一個到保健室報找護士阿姨,一問之下才知道都沾了姑婆芋的汁液,渾身發癢,於是我趕緊請這個班停止動作,「我去找專業的來!」 
聽我這麼說,全班如臨大赦,而且他們知道我又要出動農耕隊了。午休時我召集了農耕隊,帶他們到姑婆芋現場,當場教他們怎麼處理姑婆芋才不會碰到汁液,說完我便跟他一起胼手胝足,三十分鐘的午休時間就把雜草、姑婆芋全部清光光, 幹部來跟我報告的時候說:「我們連旁邊鋸下來的樹幹一起搬走了!放在那兒,不用道謝,」頭兒拍拍我的肩膀,「對啦,咱們,嘎底仔。」另一個笑笑地拍我另一邊肩膀。 放學時我照例請大家蹲下,先跟大家描述奮力清理姑婆芋的班級十分用心,接著再一一點名農耕隊成員,我唱到他們名字的時候,他們都站得很挺,也很有自信,「他們今後不再是農耕隊,是神─農─特─攻─隊」我刻意一個字一個字念完,我發現每當唸完一個字,他們更加臨風顧盼,在這裡我看到自我期許,也看到比馬龍。

校慶準備期間,這群農耕隊同學幫我把操場翻過一遍,而且每天灑水、補土,就是為了給同學一個好一點的場地辦校慶,他們從來不喊苦,也不說累,所以我很喜歡跟他們一起工作。校慶前一天場地準備得差不多了,可惜塵土仍舊飛揚,於是我召集他們,不好意思地跟他們說:「抱歉,主任有件事情想麻煩你們。」 「甚麼事?」小益問。「咖歹勢,明天可以請你們早點來幫忙灑水嗎?」「幾點?」小益又問。「六點半。」我不好意思地說,校慶在十二月中旬,加上學校在半山腰,大多數學生是搭校車到校的,六點半來的意思就是得在灰濛濛的六點多騎腳踏車出門。「主任,你做事情哪也賽阿捏?」小益說。他這麼一說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,麻煩他們灑水就算了,還要這麼早期腳踏車來,沒想到他接著竟然說:「這樣甘會赴?」他轉頭對著後面的農耕隊成員,又說:「這樣甘會赴?」在他後面的大家都搖頭,「五點才會赴。」彥彥說。我趕緊說:「五點不行啦,太早,天還沒亮!」但大家都覺得五點才有辦法把事情做完,沒奈何,我開始跟他們討價還價,最後決定六點,「你們先別吃早餐,我帶早餐來,大家吃完再做。」我心想這樣一來也差不多六點半了。沒想到小益還是念念有詞:「你做事情哪也賽阿捏?這樣甘會赴?」不過我還是堅持六點,希望他可以諒解。

隔天,我比約定的時間早個十分鐘到,把車開到操場正中央,把車子熄了火之後,聽到四處都有吆喝聲,我看不到人,只知道四處都是人。這時有個學弟從黑暗中跑出來說:「主任,你怎麼現在才來,我們都五點就到了。」說完他又消失在黑暗中,當我站在操場中央,站在黑暗之中的時候,我瞬間覺得被他們照亮,被他們包圍了,我端著裝滿早餐的箱子,身體卻輕飄飄的。 我們大家聚在操場吃早餐,我很喜歡他們臉上的笑容,而且我深信人的臉頰就像一張紙,被折的地方痕跡深了,就會成為「面相」,一個人如果經常微笑,那微笑的紋路就會成為習慣性的摺痕,很容易在臉上漾開。 吃完早餐之後我不知道要讓他們做甚麼了,「要不然你們等一下都回班上去,看看班上有甚麼要幫忙的。」聽我這麼說小益又不滿意了,他說:「你做事情哪也賽阿捏?當然是要再去噴噴水啊,水乾掉怎麼辦,你們說對不對?」這後一句他對著農耕隊成員說,於是,吃完早餐,他們一哄而散,又去灑水、填土,突然間又剩下我一個人,但我不是一個人,我身上穿著一件很多線頭勾勒的神農特攻隊背心。